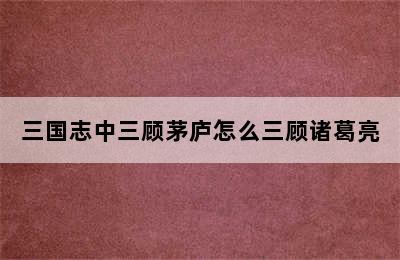
谢邀。
其实关于陈寿《三国志》的刘备三顾茅庐
,和鱼豢《魏略》中的诸葛亮主动投奔刘备的矛盾
(1),纯粹是受到裴松之的误导而作出来的
。《魏略》里诸葛亮【北行见】刘备的会面,估计就是发生在三顾茅庐之后。1,《三国志》里三顾茅庐只是刘备拜访诸葛亮,无任何词语描述是刘备征辟诸葛亮。
2,《魏略》里刘备与诸葛亮【非旧】关系无法得出是双方第一次见面,而是双方关系浅。
3,《魏略》里从诸葛亮【北行见】刘备的方向来看,诸葛亮肯定不是从隆中出发。
4,《魏略》里诸如刘备【知亮非常人】、【由此知亮】等细节,说明刘备已经认识诸葛亮。
5,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后,就是个宾客身份,并非很多人以为马上就有了官职。
6,直到刘备吞并荆南4郡,诸葛亮才有第一个官职【军师中郎将】。
7,《魏略》没有像陈寿《三国志》那样,美化刘备和诸葛亮的君臣感情,而是从零开始。
8,【情好日密】可概括从【诸生意待之】转变成【犹鱼之有水】的感情升温的时间。
仔细看《三国志》诸葛亮传,就会发现三顾茅庐过程的记载十分蹊跷。在刘备【凡三往,乃见】(2)诸葛亮询问【当世之事】(3),而诸葛亮以【隆中对】回答完毕后,刘备就只说一个【善】字就没下文了,什么表示都没有,随后直接就是刘备和诸葛亮【情好日密】(4)了。压根就无法明确诸葛亮是否答应刘备邀请而出仕。
如果刘备的三顾茅庐是亲自上门征辟诸葛亮,那起码要做到各种礼节。比如事先把征辟的礼物准备好,还有要担任左将军府的何种官职也需安排好,结果什么都没有,【三顾】行动就以刘备的称【善】一字而告终了。这可能说明刘备三顾茅庐只是拜访诸葛亮而已,或者说【三顾】之后,诸葛亮并非以刘备属下官吏的身份为刘备效力。
实际上,所谓诸葛亮出山后,开始并无任何官职,对比简雍、麋竺和孙乾3人很早就担任刘备的左将军【从事中郎】(5),诸葛亮此时就是【宾客】的身份,直到刘备【遂收江南】以后,才有第一个正式记载的官职【军师中郎将】(6)。当然,千百年来,人们总习惯性地认为诸葛亮被刘备请出山后,就立马就受到重视当了官。
要知道在两汉魏晋时期,主君征辟某人为正式下属,那就说明建立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君臣之好 】(7)的关系。而在诸葛亮在出使东吴的时候,由于刘备并没有征辟诸葛亮为府下官吏,只是宾客身份,张昭才能毫无顾忌地【荐亮於孙权】(8),来挖刘备墙角。又如鲁肃、诸葛瑾为孙权效力时也是【 始为宾客 】的身份(9)。
有趣的是,在诸葛亮以宾客身份去游说孙权前,鲁肃也是以宾客身份来吊丧刘表的(10)。因此先认知到诸葛亮只是刘备的宾客身份,再回头看《三国志》和《魏略》的区别,至少在诸葛亮的身份职位上,两者并无矛盾,无非是《魏略》里刘备和诸葛亮【非旧】的关系与一般人认知的不同。
而恰恰是裴松之可能认为三顾茅庐刘备和诸葛亮的第一次见面后,双方关系就应该好的像蜜一样,才会把诸葛亮一次【北行见备】的行为,和【备与亮非旧】(11)的关系,误认为是诸葛亮主动投奔刘备的第一次见面。其实无论是【北行见备】,还是【备与亮非旧】,这2个用词都无法得出这是双方第一次见面的结论。
在【备与亮非旧】的【非旧】一词里,
【旧】解释为:故交
,老交情
。因此【非旧】解释为两人是新交,并非熟识,关系比较浅,这说明诸葛亮在【北行见备】前已经和刘备认识。毕竟三顾茅庐两人就见了一次面,关系自然不熟,当然是【非旧】了。就如同皇帝的新装一样,一旦戳破,就会发现《三国志》和《魏略》之间并没有无法调和的矛盾。之后,裴松之可能还认为《魏略》里刘备对诸葛亮【诸生意待之】(12)和【上客礼之】(13)的待遇,就是侮辱了刘备和诸葛亮的君臣感情。但任意两人之间的亲密度都不可能刚开始就是100%的满值。即使陈寿也用了【情好日密】一词,来说明双方关系是通过时间的沉淀,来逐渐升温的。
要知道不但《魏略》这样记载,司马彪的《九州春秋》也是同样记载(14)。而司马彪写《九州春秋》的时候,蜀汉都已经灭亡了,他作为晋朝宗室,拿到蜀汉的史料书稿信件不会太难,加上诸葛亮怎么也是个名人,不太可能搞不清是谁先见谁的面。当然,《魏略》和《九州春秋》作为魏晋史书,自然不会刻意美化刘备、诸葛亮的君臣感情。
其实详加分析《魏略》的这段记载的每句话,就会发现其中的很多细节,早就显示诸葛亮已经认识刘备了。
首先
,《魏略》提到诸葛亮因为出于【荆州次当受敌】而【北行见备】,之后又提到【刘表性缓,不晓军事】(15)。诸葛亮为什么要为此特意去见刘备,又为什么要特意提到刘表呢?前文已提到,刘备在三顾茅庐后,对诸葛亮并没做什么具体安排,诸葛亮也没具体答应什么,仅是双方【情好日密】,诸葛亮只是刘备的宾客。在赤壁之战出使东吴时,还曾被张昭挖墙脚。这说明在客观上,宾客身份对诸葛亮需要忠诚刘备来说,并没有强制约束力,随时可以想出仕刘表或者孙权。而诸葛亮以宾客身份为刘备而担忧荆州,也并非难以理解。
而诸葛亮作为刘备的宾客,能够活动的范围也是很大的。在《三国志》诸葛亮传里,刘表长子刘琦可是【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16),还发生一次诸葛亮和刘琦【游观后园,共上高楼】后,被刘琦【令人去梯】(17)的事件发生,这说明诸葛亮并非一直与刘备待在新野,而是随时可以出游,比如经常待在刘琦当时的所在地襄阳。
第二
,《魏略》记载诸葛亮【北行见备】时,刘备【屯於樊城】(18),这与《三国志》诸葛亮传里,刘备在三顾茅庐时正【屯新野】(19)产生了地点矛盾,但前文提到了诸葛亮已成为刘备的宾客,而且宾客活动范围很大,那么地点矛盾就不成立了。只不过诸葛亮【北行见备】的方向却有些问题。众所周知,襄阳、樊城仅隔汉水南北相望,经常一体并称襄樊,而诸葛亮的隆中却【在襄阳城西二十里】(20)的南阳邓县,如果诸葛亮从隆中出发去樊城,似乎用【北行】不妥,用【东行】更为妥当。如此说来,诸葛亮很可能正是以刘备宾客身份在襄樊以南附近活动,得到某些荆州危机的消息后,紧急北上樊城面见刘备。
第三
,刘备与众宾客集会时提到【备与亮非旧】。前文也提到【非旧】只能说明两人关系不熟,不是【旧交】,而是【新交】,属于最近认识或者刚认识不久,不可能论证出这是刘备和诸葛亮的第一次见面。如果裴松之仅凭【非旧】一词,就把诸葛亮【北行见备】当做双方第一次见面,那就实在有些武断和牵强了。第四
,当宾客见面会【坐集既毕,众宾皆去】后【而亮独留】(21),排除诸葛亮自来熟的可能,这似乎也不像是其接受刘备面试,即双方第一次见面时诸葛亮所能够逾越干出的唐突事情,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孙权和鲁肃身上。周瑜向孙权推荐鲁肃后(22),孙权即会见鲁肃,这场合也是一场众宾客集会。同样是【 众宾罢退 】,然而与诸葛亮不同的是,鲁肃却是【亦辞出】表示告别了(23),然后被孙权叫回来。这说明诸葛亮既然能够自动留下,而刘备又能够在其面前很自然地【结毦】(24),显示了两人互相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熟悉感,更反证了诸葛亮对于刘备来说不属于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
第五
,而后诸葛亮开始对刘备提问时,刘备就突然【知亮非常人也】(25),这显然说明刘备已经多少了解诸葛亮。在刘备纳其策实施后,又出现【备由此知亮有英略】(26),其中这【由此】一词用得非常巧妙,显然又喻示双方已经认识一段时间。最终刘备【乃以上客礼之】,说明这一献策改变了刘备对诸葛亮的宾客的待遇级别。估计最令裴松之不爽的就是在《魏略》的记载中,刘备对于诸葛亮的态度仅是【诸生意待之】,以及【上客】之类的宾客待遇,似乎与《三国志》诸葛亮传的【犹鱼之有水也】(27)有着矛盾。前者【诸生意待之】在前文已提到,即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里,陈寿也是用【情好日密】来说明刘备与诸葛亮关系是通过时间的沉淀,来逐渐升温的。
通俗的说就是诸葛亮说完隆中对出仕后,双方的感情是1日好过1日。那么诸葛亮出仕之后与刘备,也就是【日密】的第1日的感情是怎么样的呢?在缺乏史料记载的情况下,诸葛亮出仕后【日密】的第1日,刘备对其感情完全可能是一张白纸。因此《魏略》用【诸生意待之】来描述刘备在初始阶段对待诸葛亮的感情,并不能说错。
当然,这【情好日密】中的【日密】具体日数也不太清楚,直到【关羽、张飞等】开始【不悦】了(28),刘备便以一句【犹鱼之有水也】挡了回去。因此【情好日密】一词完全可以概括刘备对诸葛亮从如同白纸般的【诸生意待之】,转变成浓密的【犹鱼之有水也】的这段美好的君臣感情培养升温的时间过程。
对于诸葛亮【上客】之类的宾客待遇,前文已提到即使在《三国志》里,刘备的三顾茅庐只是拜访,并非征辟,对诸葛亮的待遇没做具体安排,诸葛亮完全可以自由出仕其他势力。而在刘备和诸葛亮【情好日密】后,【关羽、张飞等】依然【不悦】,说明对诸葛亮不满的人除关羽、张飞外,大有人在。可见诸葛亮当时的宾客待遇是完全符合规格和情势的。
而诸葛亮在207年刘备拜访时提出的隆中对,再怎么吹也只是个画饼,画饼总归是不能饱饥的,刘备不可能以此来给予诸葛亮高待遇。何况诸葛亮作隆中对还是【因屏人曰】(29)的密室会谈,转化成文字记载则要靠后来补记了。因此当时只有刘备知道隆中对的内容,在其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诸葛亮即无功劳,又无资历,自然无法服众了。
当然,《魏略》记载的诸葛亮向刘备献策虽然也可能属于密室会谈,靠后来补记,但至少内容里建议清查户口、增加兵力(30)是实打实能够现用的谋略,而且务实,能够缓解刘备的燃眉之急,比隆中对这个当时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实现的画饼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刘备把它当做功劳,作为给予诸葛亮上客待遇的奖赏理由,也说得过去。
因此刘备的三顾茅庐虽然并非征辟,而只是拜访,但至少和诸葛亮建立起了关系。诸葛亮以宾客的身份为刘备效劳,按照出师表的原话就是【遂许先帝以驱驰】(31)。随着时间的深入,诸葛亮逐渐展露才华,不仅能画饼,还能务实献策,刘备自然愈发看重诸葛亮,感情和待遇也自然提升,从【诸生意待之】转变成【犹鱼之有水】的【上客礼之】。
而后人认为的刘备三顾茅庐之后,刘备对诸葛亮就有【犹鱼之有水】的君臣感情,这完全是受到陈寿的三顾茅庐对这一美好事件,所进行刻意渲染氛围的影响。陈寿的溢美导致后人沉浸在刘备和诸葛亮君明臣贤的美好情感之中,完全忽视了陈寿笔下的【情好日密】是一个经过精心编织,而是需要通过时间来沉淀感情过程的文字陷阱。
对比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本传全篇专美诸葛亮和刘备的感情,《魏略》可以说是用先抑后扬的手法来表述双方的感情。从刘备三顾茅庐,到赤壁之战前夕能够出使孙权(32),说明诸葛亮即使没有官职,也已经凭借才华成为刘备集团中极其重要的一员。当然,直到刘备【遂收江南】以后,诸葛亮才有第一个官职【军师中郎将】。
其实《魏略》和《三国志》的用意都差不多,都是表明诸葛亮是通过显露才华来博得刘备的青睐和信任,《三国志》是通过隆中对,《魏略》则是用募兵之计。只要知道刘备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只是宾客的身份,就很好理解《魏略》的记载事件是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后发生的。
将《三国志》诸葛亮传和《魏略》结合起来
,可以将过程叙述如下
: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以宾客的身份为刘备效力。作为宾客,诸葛亮能够活动的范围是很大的。当时诸葛亮并非在襄樊西面的隆中,而是在南面活动。当诸葛亮觉得荆州受到北方威胁越来越大时,临时起意而北上,向正驻扎在樊城的刘备献策。刘备从此觉得诸葛亮有真才实学,在纳谏后将诸葛亮升为上级宾客。
引用史料
:(1)裴松之: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於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
(2)三国志诸葛亮传: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3)三国志诸葛亮传:三顾臣於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
(4)三国志诸葛亮传: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於是与亮情好日密。
(5)三国志简雍传:先主至荆州,雍与麋竺、孙乾同为从事中郎,常为谈客,往来使命。
(6)三国志诸葛亮传: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7)晋书向雄传:雄初仕郡为主簿,事太守王经。及经之死也,雄哭之尽哀,市人咸为之悲。后太守刘毅尝以非罪笞雄,及吴奋代毅为太守,又以少谴系雄于狱......时吴奋、刘毅俱为侍中,同在门下,雄初不交言。武帝闻之,敕雄令复君臣之好。
(8)袁子曰:张子布荐亮於孙权,亮不肯留。人问其故,曰: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
(9) 三国志吴主传: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
(10)三国志鲁肃传: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
(11)魏略曰: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
(12)魏略曰: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
(13)魏略曰:乃以上客礼之。
(14)裴松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
(15)魏略曰: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
(16)三国志诸葛亮传: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
(17)三国志诸葛亮传: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
(18)魏略曰:刘备屯於樊城。
(19)三国志诸葛亮传: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原见之乎?
(20)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21)魏略曰: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
(22) 三国志鲁肃传:瑜因荐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
(23)三国志鲁肃传: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
(24)魏略曰:备性好结毦,时適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
(25)魏略曰: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毦而已邪!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答曰: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耳。
(26)魏略曰:备由此知亮有英略。
(27)三国志诸葛亮传: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原诸君勿复言。
(28)三国志诸葛亮传:於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
(29)三国志诸葛亮传: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
(30)魏略曰: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
(31)三国志诸葛亮传: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32)三国志先主传:先主遣诸葛亮自结於孙权。
